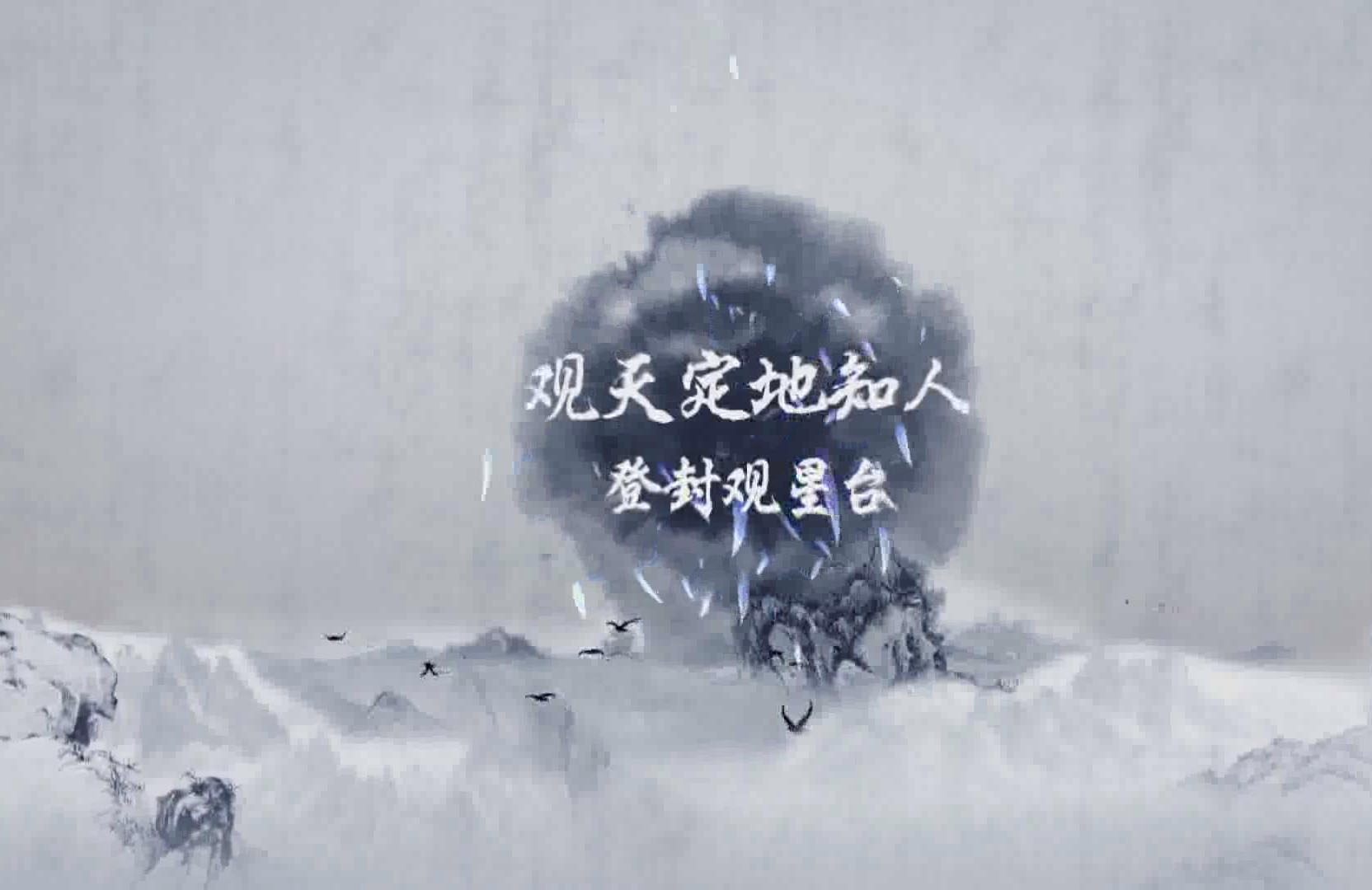莲鹤方壶
时间:2015-12-19 字体:大 中 小

郭沫若先生“点评”过莲鹤方壶。都说郭老评得经典,无人再评,只好让郭老在这儿“再评”一次了!
郭老的“点评”,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其实,不靠“阶级立场”,不是不能说莲鹤方壶的。
鹤,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语言。在中国文化中,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象与意象之一--鹤鸣九皋,一鹤冲天,松鹤延年,鹤发童颜,仙鹤道僮,闲云野鹤,梅妻鹤子,乘鹤羽化乃至驾鹤西去,风声鹤唳,煮鹤焚琴等。郭沫若先生将莲鹤方壶上的那只青铜之鹤,释义为“踌躇满志,睥睨一切,践踏传统于其脚下”,“争求解放、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”,将其“意识形态化”,倒也未必就是“绝对真理”。
《逸周书·王会》曰:“周室既宁,八方会同,各以职来献。欲垂法厥世,作王会。成周之会,上张赤,张阴羽。”--西周初年,洛邑(成周之会)建成,周成王大会诸侯,是谓“成周之会”。“成周之会”是王朝的国家典礼,在这样的典礼上,成王为大会诸侯搭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“帐篷”。这“帐篷”,为何偏偏装饰鹤之羽呢?
西晋初年五经博士孔晁曰:“,帐也;阴,鹤也。以羽饰帐。”《易经》云:“鹤鸣在阴。”《相鹤经》亦云:“鹤,阳鸟也,而游于阴……鹤七年一小变,十六年一大变,百六十年变止,千六百年形定。体尚洁、故其色白;声闻天、故其头赤;食于水、故其喙长;栖于陆、故其足高;翔于云、故毛丰而肉疏。大喉以吐故,修颈以纳新,故寿不可量。行必依洲渚,止不集林木,盖羽族之宗长、仙家之骐骥也。”
鹤,是游走阴、阳两界的仙鸟;鹤,是王者、仙家的骐骥!《相鹤经》一说浮丘公所作,一说为南北朝宋人所为--“托仙人浮丘公传于王子晋,王子晋藏经于嵩山石室,有淮南八公采药经此获得,遂传于世”。不管哪一说,都不远浮丘公。
王子晋,灵王太子,在缑山(在偃师)乘白鹤仙去,接引他的,正是浮丘公。“王子乔者,太子晋也。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(嵩山)。”沟通阴、阳两界的鹤儿,此时由周初王者的象征、仙家的骐骥,演化为升仙的“鹤驾”--没有仙鹤这一“道具”,王子晋也许是不能羽化为仙的。
莲鹤方壶之铸造年代,约在王子晋乘鹤升仙前后。
郭老说莲鹤方壶上的青铜之鹤,“踌躇满志,睥睨一切,践踏传统于其脚下”,俺怎么觉得,它仙气飘飘,像一只站在酒坛上贪酒的“醉鹤”呀。杜康酿酒醉刘伶,醉了,也就仙了。
莲鹤方壶神仙世界的无字之碑
“炼汞烧铅四十年,至今犹在药炉前。不知子晋缘何事,只学吹箫便得仙。”这是素信神仙的唐末大将、诗人高骈的疑问。
高骈炼汞烧铅四十年,相信仙丹已经灌到肚子里不少,但还在炼、还得吃,成仙之路还遥遥无期。这,不能不让他发出天问:王子晋,小小年纪,没有炼汞烧铅,怎么只学吹箫,跨上鹤驾,就成神仙了呢?
有唐一代,不只是高骈,就是女皇武则天、诗仙李白等,也是王子晋的“粉丝”——武则天在王子晋吹箫、驾鹤升仙而去的缑山上扩建庙宇,御笔亲撰《升仙太子之碑》;李白更直接,在《感遇》中直呼“吾爱王子晋”:“吾爱王子晋,得道伊洛滨。金骨既不毁,玉颜长自春。可怜浮丘公,猗靡与情亲。举首白日间,分明谢时人。二仙去已远,梦想空殷勤。”李白不只是嘴上说“爱”,还付诸行动,拔腿就“追”,非要当王子晋的邻居。《送杨山人归嵩山》云:“我有万古宅,嵩阳玉女峰。长留一片月,挂在东溪松。尔去掇仙草,菖蒲花紫茸。岁晚或相访,青天骑白龙。”玉女峰、子晋峰、浮丘峰相毗邻,都在嵩山太室山西部。
王子晋驾鹤、吹箫,此简简单单,为何就能飘然成仙?
贾湖骨笛的发现,也许能帮我们找到答案。
《礼记·乐记》云:“禽兽知声而不知音。”“音”与“乐”,从根本上讲,是人的心声:“情动于中”,就要“形于言”;“言之不足”,就要“歌咏之”;“歌咏”还不足以抒发情感,那就“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”。
中国最古老的音乐,是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说的昔葛天氏之乐:“昔葛天氏之乐,三人操牛尾,投足以歌八阙……”一般认为,该乐与祭祀与原始宗教信仰相关。
上古部落首领的名号,无不与其发明创造有关。神农氏种植五谷、有巢氏筑巢建舍、燧人氏钻木取火。他们的创世功勋,都隐含在名号里。但被尊为“乐神”的葛天氏,其名号来源,却一直是个“话题”。
如果葛天氏发明了乐舞,那么“葛天”,就该与乐舞有关。但也有人从《诗经·采葛》出发,以为“葛”既然是一种草,它的植物纤维可以织布裁衣,那么葛天氏部落就不只是乐舞的发明者,也是织布、衣裳的发明者,并由此推测,葛天氏用“葛”制衣,故称“葛天氏”。若为“葛氏”,这一解读,也许不无道理。“葛天”当与“神农”、“有巢”一样,表述的也该是一个部落的创世功勋。如果“葛”是草,用它装饰“天”,有什么道理?再说,在中国文化语境中,“天”,大得不得了,小草,还真能遮“天”乎?
话再说回来,如果葛天氏发明了乐舞,那么“葛天”就当被解读为以“乐舞”敬“天”、颂“天”——就是我们不知道“葛”是什么,这解读也不会南辕北辙——既然葛天氏被奉为“乐神”,不会因他善于自娱自乐,而是因他长于“以乐娱神”、“以乐娱天”!
“葛”是什么?不能瞎说。但“葛天氏”生活在今天的河南长葛一带,却是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。
而这儿,恰恰不远出土贾湖骨笛的贾湖遗址、出土鹤鱼石斧图(该图绝对年代在6000年前后,被学界视为中国画的鼻祖)的河南汝州。“贾湖骨笛、鹤鱼石斧图都是史前最为重要的神器。贾湖骨笛是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与天沟通的神器,用鹤的尺骨制成;鹤鱼石斧图彩绘在陶缸上,缸内装成人骨骸,作为成人瓮棺使用。而使用瓮棺,一般认为与灵魂升天的祈望相关。”中国科技大学教授、考古学家张居中先生说。
这一带的史前神器,为什么总与鹤发生关联?这是个问题,也不是个问题——不如此,鹤,怎么会影响中国直到今天!
但不管怎么说,贾湖骨笛,也是可以叫做“贾湖骨箫”的——在两者之间,学者只不过是选择“贾湖骨笛”做了它的名。作为笛子,它没有笛膜,没有横吹孔,只能竖吹;作为洞箫,它没有竖吹孔嘴。羌笛也是竖吹的,至于笛子横吹,是后来的事。
从乐器发展进程看,贾湖骨笛应该发展成了中国洞箫。而羌笛,这个外来的乐器,占据了中国“笛”的名号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王子晋学吹箫、乘鹤驾就能升仙,不轻松,实很累。他能“一鹤冲天”,凭助的,是先民们已经打造了数千年的“神器”;他能“金骨不毁”,寄托的,是先民们已经追求了数千年的“梦想”。
“二仙去已远,梦想空殷勤。”——驾鹤成仙,是一个时代的梦想与追求;梦想与追求化为造型艺术,就是莲鹤方壶盖顶上的那只昂首挺立的青铜之鹤;青铜之鹤寄托与承载的,是一个时代飘然成仙的梦想与追求。
莲鹤方壶青铜时代的“初发芙蓉”
奇士不可杀,杀之成天神。
王子晋聪明冠世,体恤百姓,作为太子,在战乱四起的春秋,他被寄予过太多的期望。他的不幸早逝,被神仙家当成了“炒作”的题材;他的吹箫、驾鹤升仙,正应和了当时朝野的所想所愿。
神仙家借此朝野关注的这么一“炒”,不但王子晋成了神仙,神仙思想也很快得以普及——这在中国历史上,是第一次神仙思想大众化。
其实,神仙思想大众化在当时没有什么不好,它从本质上来说,能成为摧毁旧世界,建设新世界的一种力量。就是信仰神仙,当时也没什么不好——李白不信神仙,能写出他那豪迈之作,还会成为“诗仙”吗?
神仙思想,激荡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那份浪漫主义,让中国语言艺术、音乐艺术与造型艺术等,都瑰丽起来。
南北朝梁国文学家殷芸《小说》云:“有客相从,各言所志,或愿为扬州刺史,或愿多资财,或愿骑鹤上升。其一人曰:‘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。’欲兼三者。”其实,神仙思想并不消极,它很难消解现实的妄想,甚至是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论及莲鹤方壶说:
鲍照比较谢灵运的诗和颜延之的诗,谓谢诗如“初发芙蓉,自然可爱”,颜诗则是“铺锦列绣,亦雕缋满眼”。《诗品》:“汤惠休曰:‘谢诗如芙蓉出水,颜诗如错彩镂金。’颜终身病之。”这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。
从魏晋六朝起,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,那就是,认为“初发芙蓉”比之于“错彩镂金”,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。在艺术中,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人格,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。陶潜做诗和顾恺之作画,都是突出的例子。王羲之的字,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、那么有装饰性,而是一种“自然可爱”的美。这是美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解放。
这种美学思想的解放,在先秦哲学家那里就有了萌芽。从三代铜器那种整齐严肃、雕工细密的图案,我们可以推知先秦诸子所处的艺术环境是一个“错彩镂金、雕缋满眼”的世界。先秦诸子对于这种艺术境界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态度:一种是对这种艺术取否定的态度,如墨子,认为是奢侈、骄横……反对一切艺术;庄子重视精神,轻视物质表现;老子说:“五音令人耳聋,五色令人目盲。”
另一种对这种艺术取肯定的态度,这就是孔、孟一派。艺术表现在礼器、乐器上,孔、孟是尊重礼乐的。但他们也并非盲目受礼乐控制,而要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,进行分析批判。总之,不论是肯定艺术还是否定艺术,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批判的态度,一种思想解放的倾向。这对后来的美学思想,有极大的影响。
但是实践先于理论,工匠艺术家更要走在哲学家的前面。先在艺术实践上表现出一个新的境界,才有概括这种新境界的理论。现在我们有一个极珍贵的出土铜器,证明早于孔子100多年,就已从“错彩镂金、雕缋满眼”中突出一个活泼、生动、自然的形象,成为一种独立的表现,把装饰、花纹、图案丢在脚下了。这个铜器叫“莲鹤方壶”。它从真实自然界取材,不但有跃跃欲动的龙和螭,而且还出现了植物:莲花瓣。表现了春秋之际造型艺术要从装饰艺术独立出来的倾向。尤其顶上站着一只展翅的仙鹤,象征着一个新的精神,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。
宗白华先生寻求“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”,上推至莲鹤方壶;俺从贾湖骨笛出发,诉求中国神仙思想借助“仙鹤”,怀念先民健康童年,却在不经意间摧毁了一个旧世界,停靠点也是莲鹤方壶。
一个上行,一个下移,都停在莲鹤方壶。
所处时代:春秋时期;器物规格:高120cm、口径31cm;出土时间:1923年
出土地点:河南省新郑城关李家楼村
专家点评
此壶(莲鹤方壶)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,予人以无名之压迫,几可窒息。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,以植物为图案,器在秦汉以前者,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。而在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(仙鹤),翔其双翅,单其一足(郭沫若先生观看莲鹤方壶照片,写下此语,照片上莲瓣遮挡鹤之一足,故有“单其一足”,此鹤实乃双足而立也),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,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。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,正踌躇满志,睥睨一切,践踏传统于其脚下,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。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,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。
盖顶一鸟耸立,张翅欲飞,壶侧双龙旁顾,夺器欲出,壶底两螭抗拒,跃跃欲试,全部格局,在庞然大器的附着上,有离心前进动向,最足象征争求解放、迎接曙光的时代精神。
点评专家:
中国科学院前院长 郭沫若
?